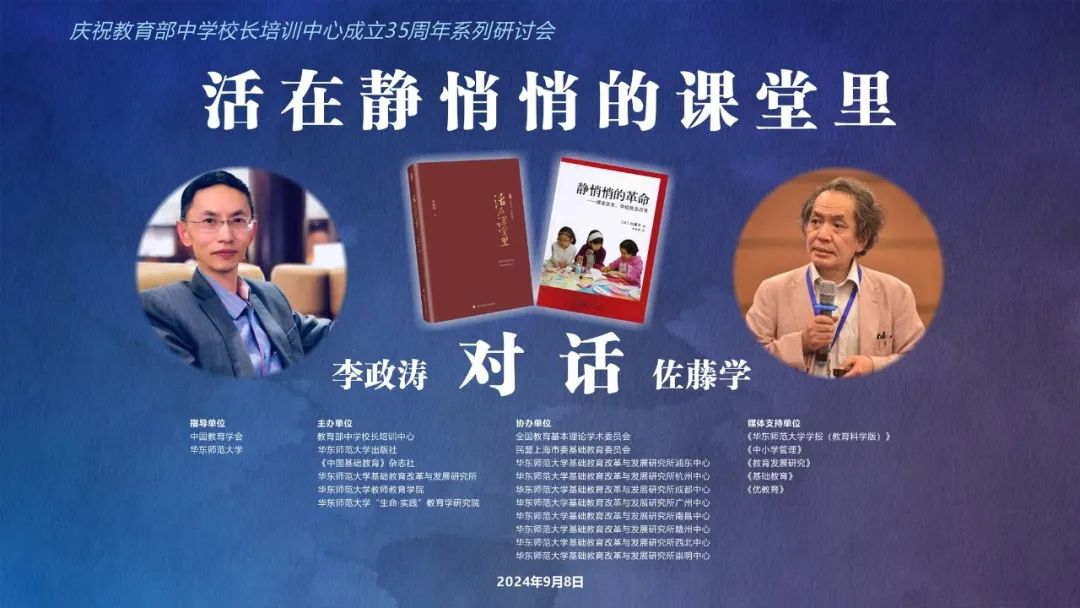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此前一天,由中国教育学会、华东师范大学联合指导的“李政涛对话佐藤学:活在静悄悄的课堂里”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逸夫楼举行。两位教育专家共话新时代教育改革与课堂变革的历程,探讨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挑战及机遇,解读如何“活在静悄悄的课堂里”,对话中有倾听、有共鸣、有反思,更有新观点新思想的激发和生成。多位知名专家和校长现场分享感受,超过30万人线上见证全程。作为会议主办方之一,《中国基础教育》编辑部全程参与对话的策划、组织和宣传等工作,现特将此次对话内容进行独家报道。

李政涛:对话人,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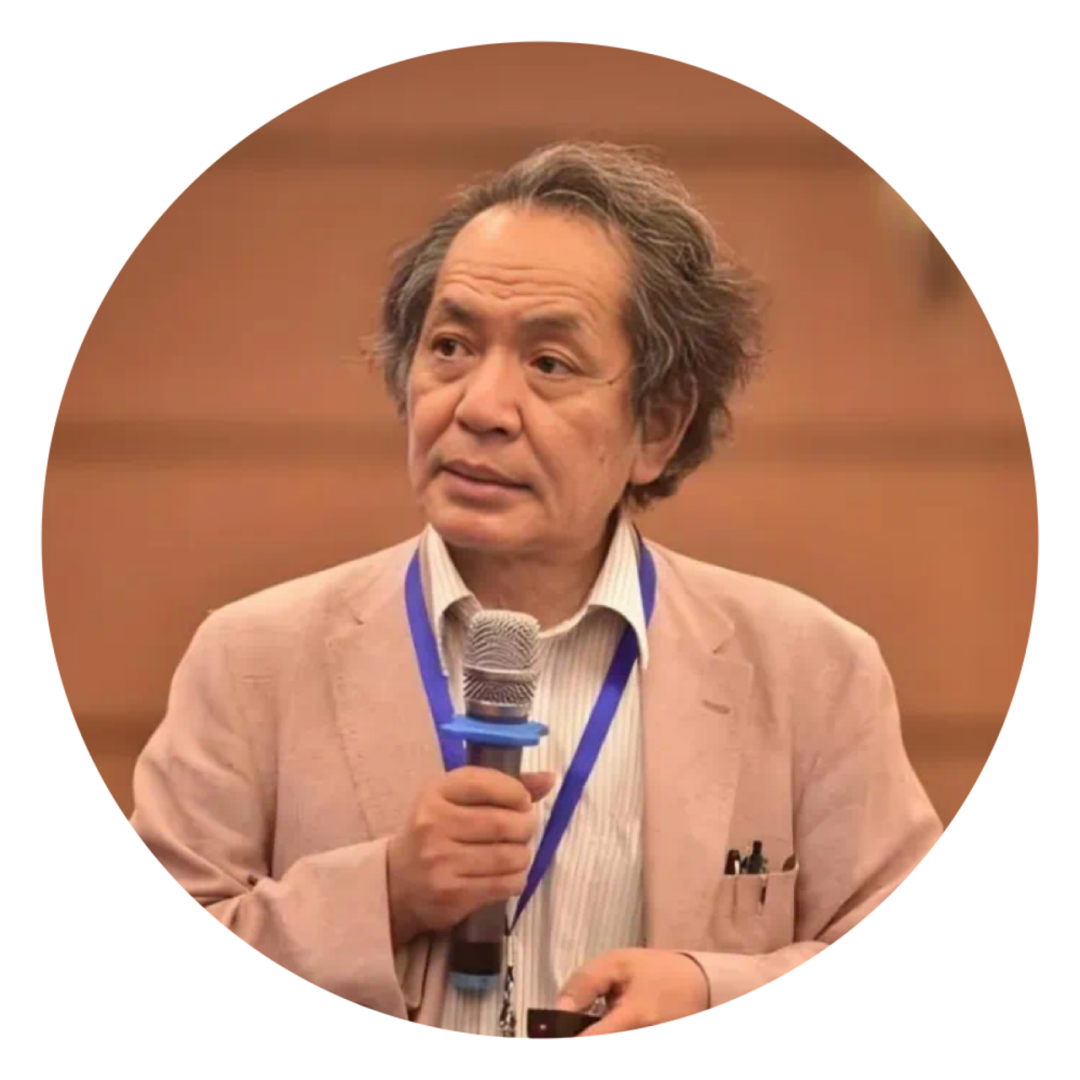
佐藤学:对话人,日本教育学会原会长,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孙金鑫:主持人,《中国基础教育》主编
/
/
为什么要“对话”?
主持人:很荣幸能主持这场高端对话。佐藤学先生可能是当下中国教育人最熟悉的日本教育家。自从2003年《静悄悄的革命》在中国出版以来,他的许多著作已成为很多中国校长教师的必备书,他也亲自走进过中国几百所中小学校的课堂。应该说他是与中国校长和教师的物理距离和心灵距离最近的外国当代教育家。
李政涛教授作为在中国校长和教师中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教育学者,不只是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更是持续30年的“新基础教育”实验以及创建已经20年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核心人物,他最近出版的《活在课堂里》再次引起校长教师的广泛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两位对话人在教育理想、研究旨趣、实践影响力方面有着很多相近之处,都深度关注课堂改革、关注学校发展、关注师生生命状态。今天其实有许多可讨论的话题,也有很多可选择的研讨形式,但两位为什么要采用“对话”这种形式?对这次对话有什么期待?
李政涛:这场对话的缘起是一本书,就是《静悄悄的革命》,今天终于有机会和作者佐藤老师面对面地深度交流,我特别高兴。如果说我对这次讨论有所期待的话,那么这个期待就是“对话”。什么叫对话呢?
对话首先意味着倾听,没有倾听就没有对话。我和佐藤老师都非常重视倾听。今天我特别希望在我和大家的认真倾听中,能听出他对于课堂的更多更新的真知灼见。
对话也意味着共鸣,没有共鸣就没有对话。我之前是通过阅读佐藤老师的书籍、通过他的文字来跟他对话的。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阅读《静悄悄的革命》的过程中,我不断产生许多方面的共鸣,比如说关于倾听的共鸣。
对话还意味着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对话。我和佐藤老师的差异,不仅是我们个人之间的差异,也是各自所属团队的差异,还可能是中日两国学者的差异。有了差异,才有助于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教育共同体对课堂和教育的理解。
对话更意味着创作或者创造。不仅教学是即席创作,真正的对话研讨也是即席创作。今天我们不仅是对话者,也是创作者,包括今天的致辞人、主持人、点评人、提问人、总结人,都是这场对话的即席创作者。佐藤老师曾经指出,课堂教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纺织工式、织布式或裁缝式的课堂,一种是交响乐式的课堂。今天我们大家其实就结成了一个关于课堂的、跨国的、跨学校的创作共同体。我们借助这场研讨,共同创作出关于课堂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和新见识,这可能是我和佐藤老师对这次对话最大的共同的期待。
佐藤学:是的,我和李老师之所以能进行对话,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其一,我们都非常关注课堂。李老师的著作是《活在课堂里》,我的《静悄悄的革命》中文版的副标题和日文原版的书名本身是“课堂改变,学校就会改变”。
其二,我们都非常关注倾听。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独白的时代,对倾听的关注远远不够。我曾经提出过“倾听的教育学”,李老师出版了《倾听着的教育》,倾听是对话的出发点、起始点,只有相互倾听才能孕育出对话,而只有对话才能孕育出学习,也只有在对话基础上才能够建构出共同体。
其三,“生命·实践”教育理论和我的教育学观点有很多相近之处。追溯近代教育education的词源educare,我理解到,教育的本源就是为了培养生命、丰富生命,这与李老师团队的“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理论有高度共通点。
/
/
教育人要“活”在哪里?
主持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看来是两位教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话这种形式。其实你们之间有很多可探讨的话题,但这次为什么要把主题聚焦在“活在静悄悄的课堂里”?
佐藤学:50年前,我开始研究教育学,开启了向老师、向学生学习的旅程。但50年前的日本教育研究者,多是以指导者的身份进入学校,很难能低下身、弯下腰来,认真地、谦虚地向师生学习。一个合格的教育研究者,不能一直居高临下地到学校去指导。研究者和师生之间的权力关系如果不改变,那么很多问题是无法得到真正解决的。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关系,50年来我一直在“战斗”,甚至是孤独地战斗。
李政涛:佐藤老师和我都是教育研究者,都教教育学。对于教育研究,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书斋”里的研究。我在德国访学的时候,感到德国的很多教育学教授是典型的“书斋式”学者,就是从论文到论文,从著作到著作,基本上不到中小学去,不到课堂里去,这是一种研究方式。第二种是“田野式”研究,扎根于日常课堂的研究。倾听在哪里发生?不是在书斋里,是在现场,在课堂现场、课堂的田野里发生。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更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价值。
为什么我和佐藤老师都很关注课堂?相对而言,人们对于课堂和教育研究的关系、和教育学的关系,特别是书斋与田野的关系的认识,普遍存在着几个误区:一是轻视,重书斋而轻田野,理论工作者通常会有一种“理论的傲慢”;二是割裂,把书斋和田野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非此即彼,要么是书斋,要么是田野;三是偏见,重田野而轻书斋,实践工作者往往认为许多理论脱离实践,理论无用,存在“实践的傲慢”。
怎么走出这些误区?首先我跟佐藤老师一样,都非常认同课堂、田野对于教育研究的价值,对教育理论创生的价值。其次,要在书斋与田野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的载体,那就是课堂,用课堂把书斋和田野连接起来、贯通起来,再创生出新的理论、新的实践经验。这两种生活方式是可以兼容的,我和佐藤老师的两个团队就是穿梭在两种生活方式之中。我希望大家,既包括理论工作者也包括实践工作者,也都能够兼容这两种生活方式,既有田野的生活,也有书斋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理想的教育、理想的教育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穿梭在书斋与田野之中。
佐藤学:我认为,教育学研究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教育实践的研究,一类是对教育政策的研究。好的教育研究一定要和实践密切相关。我们如果只在书斋里进行研究,可能就无法真正了解教育。越是优秀的教育学者,其研究经历越是和实践密切相关,如国际上的杜威、皮亚杰、维果斯基、布鲁姆、弗莱雷,和中国的陶行知、蔡元培、陈鹤琴等,他们都是以教育实践为核心开展自己的教育研究的。
但是,教育实践中蕴含非常多复杂的要素和结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研究者要具有非常深厚的学术功底,才能真正做好教育实践研究。所以,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最顶尖的大学在开展教育实践研究,如美国做教育实践研究做得最好最有代表性的学校是哈佛大学、做教育政策研究最全面的是斯坦福大学,英国做教育实践研究最扎实的是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日本做教育实践研究最扎实的是东京大学。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二者之间有三种关系。第一种关系,就是理论的实践化,theory into practice。大家常常做的是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但我个人不推荐这样的研究。因为在理论实践化的过程中,研究者和现场教师的关系就会变成理论高高在上的上下级权力关系。第二种关系,就是实践的理论化,theory through practice。这也有不足的地方,因为研究者作为一个外部介入者是很难融入到教室当中的。第三种关系,是实践中的理论,theory in practice。教师的实践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理论,但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是在生成理论,而只是把这种理论当成自己的实践性知识。研究者应该深入地去观察和了解这些属于教师自身的理论。
李政涛:受到刚才佐藤老师对于理论和实践的分类的启发,我认为,把教师和理论连接起来的方式可能有三种。第一种是“对教师”的知识,是从外部灌输给教师的知识。第二种是“为教师”的知识,是基于教师的需要量身定做的知识。第三种就是佐藤老师说的“教师自己的理论”,是“教师自己的知识”,是在他自己的课堂实践中创生出来的知识。只有这样,教师才能真正成为实践知识的创生者,而不只是某种理论知识的传递者、践行者和转化者。三种类型都是理实相生的方式,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
/
怎样理解“静悄悄”?
主持人:两位教授所谈的这些,是对教育研究者怎样研究,教育人应该怎样“活”、应该过怎样的教育生活的深刻解读。我们不只要“活在课堂里”,因为课堂是链接书斋与田野的最好载体;还要活在一个“静悄悄”的课堂里。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静悄悄”?
佐藤学:在《静悄悄的革命》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就对“静悄悄的革命”有一些思考。20世纪80年代,我对32个国家的教学录像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在这些课堂上,80%的时间都是老师在说话、在讲解。但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推进,教育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许多国家的教室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变化:过去的秧田式的排排坐的教学方式突然间消失了,变成了四人一小组的座椅排列方式,课堂上教师大概只用10%的时间在说话。这些变化说明,世界教育出现了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或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转型、从以知识理解为目的的学习向以探究为目的的学习转型、从个体学习向协同合作学习的转型。
这些变化最开始大概发生在澳大利亚,此后迅速辐射到各个发达国家。因此当我计划在中国出版《课堂改变,学校就会改变》这本书的时候,我预测并希望中国的基础教育也将发生这样的一个静悄悄的革命。所以我用了“静悄悄的革命”作为中文版书名,希望能打动中国老师们的心。但是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的预期没有完全实现,中国的教育改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另外,我个人也很喜欢“静悄悄”这个词,我认为优秀的教师都是安静的教师,都是善于思考的教师,思考的时候自然是静悄悄的。那些嗓门大的老师并不一定是优秀的老师。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和保护那些看起来非常安静的、没有话语权的老师。
李政涛:我原以为佐藤老师只是对课堂的静悄悄进行解读,没想到他把静悄悄课堂放在一个宏大的社会变革的背景之下来表达。我也没想到佐藤老师对中国课堂的表达如此之坦率,我非常理解佐藤老师的这种观感,可能他看到的有些课堂还存在很多问题。实际上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一直在为改变传统课堂教学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仅以我参与的“新基础教育”实验为例,作为发起者的叶澜老师在30年前就提出,中国中小学要从近代型学校走向现代型学校,现代型学校的标志是要破除传统课堂、建构现代课堂。为此叶澜老师提出要把课堂还给学生,具体是要把提问权还给学生、质疑权还给学生、评价权还给学生、工具权还给学生、总结权还给学生。在中国,还有很多团队在做类似的探索,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
同时,我对佐藤老师对“静悄悄”的理解深有同感。这个话题涉及什么是理想的课堂。理想课堂要处理好几对关系,如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预设与生成的关系、动态与静态的关系。课堂上的动,是互动,是活动,也是灵动。课堂需要多种多样的互动,如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课堂需要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辩论、教育戏剧、课本剧;课堂也需要多种、多项、多维的灵动,需要创造的火花。互动,产生课堂的活力;活动,产生课堂的体验;灵动,产生课堂的创造。他们共同通向学生成长,这就是“动”的意蕴。
我们谈静悄悄,并不意味着否认或否定互动、活动和灵动的价值,只不过相对而言,我们对“静”的理解和探讨比较少。静悄悄具有多重“课堂意义”。静悄悄与学-学习有关,只有静下心来,才能真正有效地学习;静悄悄与思-思考有关,只有安静才能沉思,所以才有“静心思考”的说法;静悄悄与听-倾听有关,只有静心才能倾听;静悄悄与深-深度有关,静水流深,没有静就没有深度学习、思考、倾听。静悄悄与慧-智慧有关,静而生慧。我们现在的课堂可能不缺热闹,缺的是静悄悄的课堂的氛围和文化。当孩子渐渐长大以后,他们要面对和解决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因此现在特别需要在静悄悄的课堂氛围中进行深度学习,才能更好地成长。
佐藤学:李老师所提到的对于“静悄悄”的解读非常重要。过去30年我走访了世界各国的教室,看到了非常多优秀教师的课例。这些优秀课例呈现出来的课堂都是静悄悄的。甚至有欧洲的老师认为,教室应该是仅次于教堂的第二安静的地方。
主持人:受两位教授启发,我也想说几句关于“静悄悄”的想法。一是静不代表静止,静悄悄的革命,区别于以往我们所说的激进式的革命,在时间维度上可能是渐进的、缓慢地进行的,但不代表不进行,而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悄悄变化的过程。二是静不代表静默,静悄悄的课堂,可能表面上与传统的安静课堂相似,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不是思想停摆的课堂,不是死气沉沉的课堂,而是充满思维活力和创新张力的课堂。三是我们今天谈要有静悄悄的课堂,但不代表所有课堂都要静悄悄。静悄悄的课堂更多可能指的是学科知识学习的课堂,有一些课堂如劳动的课堂、体育的课堂、社会实践的课堂等,就必须是热气腾腾、生龙活虎的动的课堂。
/
/
如何建构“静悄悄的课堂”?
主持人:静能生慧,刚才的探讨给我们很多启发。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很多课堂还很难做到“静悄悄”,但中国教育人确实一直在努力。促进中国的课堂改革,最关键的应该是什么?
佐藤学:教师改变,课堂一定会改变;课堂改变,学校就会改变。其实过去20年中国教育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教师队伍的质量提升。我认为中国教师队伍是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教师队伍。教师该如何改变?我们一定要学会学习的革新,要让学校和教师形成合作的网络,或者是校际交流的网络。我期待所有教师都能够勇于创新、敢于创新、乐于创新。相关部门和学校要给教师面对失败的勇气,给教师改革的勇气和底气。
李政涛:佐藤老师所言的改革勇气,对于教师成长至关重要。这种改革,是教师的自我改革,甚至是自我革命,改出或革出新本领、新能力。在“双新”,即新课程、新教材的时代,教师要练好新基本功。中国课堂有“老问题”,如缺乏活力、缺乏自主、缺乏思维培养等,尤其是后者,比较容易被忽略,所以,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特别强调要“改变思维”。但现在中国课堂又有新的问题:缺乏融通,首先缺五育之间的融通,五育往往是割裂的;再者缺思维、情感、审美的融通,很多课堂要么抓思维,要么抓情感,要么抓审美。教师缺融通能力,缺少新基本功,比如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基本功,和各种新理念相应的如大单元教学、项目化学习、大概念教学、学科实践等教学新基本功,这可能是未来课堂改革和教师教育要努力的方向。
主持人:刚刚李老师提到理想课堂要处理好几对关系。在中国,很多区域和学校提出要打造理想课堂,所以大家也很想知道佐藤老师心目中的理想课堂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向着什么方向努力?
佐藤学:我的回答可能会让大家失望,我从来没有想过理想的或者说完美的课堂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每个人认为的理想课堂都会不太一样。比起去想象理想的课堂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更关心的是现在发生了什么、教师的现实需求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该如何去解决。我主要做的事是对现在的课堂进行分析,然后去解决问题。比如:老师们的声调应该先降下来。我感觉中国的老师太慷慨激昂了。对于教师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要去说去表达,而是要去倾听(学生内在的声音),去捕捉(学生的思考)。同时,教学课题的深度和拓展度一定要提升,只有具有挑战性、能促进学生深入思考的课题,才能让学生静下心来,课堂才能够安静下来,学生才能够深入地去思考。
主持人:佐藤老师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和老师们关注理想课堂,其实是不矛盾的,一种是问题解决式思维,一种是愿景导向式思维,我们谈问题解决,往往是在愿景牵引下的问题解决。很多老师也关心,在日常教研中,我们该如何观察课堂?甚至有老师提到一个非常具体但现实的问题:在进行课堂观察时,是该坐在教室前面观察,还是后面观察?
佐藤学:我们进入课堂去观察,并不是为了去评价老师的教学方法是否优秀,而是去观察在学生和教师互动的过程中,学习在哪里发生了?学习在哪里受到阻碍了?学习的基本事实是什么?学习的可能性在哪里?如果你坐在课堂后面的话,你不能学到任何知识,因为你只能看到老师而看不到学生。因此我常常建议老师们去观课的时候,既不要站在最前方,也不要站在最后方。
李政涛:佐藤老师曾经提过,要以蚂蚁之眼来看课堂,要非常微观、非常精细、非常注重从教学细节挖掘出它的意涵。根据我们团队的经验,观察课堂,不是看老师在课堂上的教,也不是看学生在课堂上的学,而是看教与学的互动,你无论坐在哪里,都是观察互动,都要有利于洞悉互动。
主持人:很多老师也想通过今天的对话,了解中日课堂之间的差异,也很想了解当前日本课堂的主要特点,请两位教授给大家做简单解读?
李政涛:我没有实地听过日本老师的课,更多是通过文献来了解日本课堂。我感觉中日课堂的根本差异,可能与文化传统尤其是教育文化传统有关,这是课堂差异背后的文化差异。
佐藤学:说实话,我在看课的时候,无论看中国的课堂还是看日本的课堂,我只把它作为课例来看,并没有把它作为不同国家的课去看。因为文化的不同,两国的课堂一定会不同,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两国共同面临的教育课题,比如两国在课堂与学习的革新方面的问题。
日本有一个让中国同行很难想象的地方,就是日本儿童的生活贫困率是非常高的。如有调查显示,在东京都和大阪府的学龄儿童中,可能有1/3的孩子无法负担午餐费用。家庭经济状况会对学生的学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的教师更加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教学生活,让学生变得幸福。这可能是他做课的切入点,包括他开展教学生活的切入点。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改革相比,日本的教育改革起步相对较晚。当前日本的中小学课堂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根据文部科学省的文件要求,最近在推动“能动性学习”(active learning),就是基于主体性对话性深度学习。二是当前使用信息技术工具如平板的频率非常高。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日本学校使用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的时间非常少,但疫情之后现在日本学生几乎是人手一个小平板。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我们一定要更加慎重地去对待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问题。
/
/
让教师成长起来
主持人:教师是改变课堂的关键,中国正在庆祝第40个教师节,目前中国专任教师总数已经达到了1891.78万。对于教师,两位教授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建议?
佐藤学:教师的工作是一个接受的工作:接受全体学生、接受自己的课堂环境、接受自己的学校、接受自己所在的社区、接受自己所处的社会。教师要能够接受学生的不同、接受工作环境的不同、接受地区的不同。另外,教师特别期待自己被尊重、被信赖、被爱戴。教师只有去接受学生、尊重学生、信赖学生,才能获得学生的尊重、信赖与爱戴。在此,我特别期待各位老师能够成为受学生敬重和信赖的人。
李政涛:教师节是表彰的节日,也是学习的节日,我们要向教书育人的楷模学习、向教育家学习,学习他们怎么样去接纳学生、信赖学生、尊重学生,甚至学习他们怎么接纳教学生涯的失败。这样的学习,就会让我们的节日变成成长的节日。成长是教师的天职,教师通过教育教学让学生成长,也让自己成长。我们共同祝福教师自我的成长和拥有促进学生成长的能力。
主持人:李老师在《活在课堂里》开篇就提到:每个人都有自己活泼泼的生命,没有一个课堂可以复制,没有一个生命可以重来。教师要学会接受学生、接受环境、接受各种不同,更要学会接受自我、悦纳自我、成长自我。
马克斯·范梅南说“教学就是即兴创作”,我们这个对话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即兴创作。我们希望在中国的课堂里,在中国基础教育的广阔天地里,会有更多有价值的即兴创作呈现出来。每个校长、每个教师、每个学生,甚至每位管理者,都能在静悄悄的课堂中,活出自己真正活泼泼的生命。
文章来源:《中国基础教育》2024年第10期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文章末尾固定信息


评论